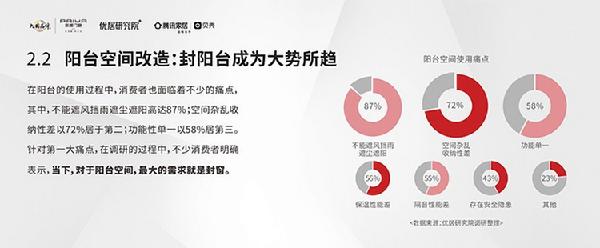
孟买“史密斯”一直从事印度棉花贸易,将资金投入中国市场,与行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,是三位之中唯一未因债务而破产者,但他却意外地卷入了“休斯夫人号事件”。
1784年的某一天,英商船“休斯夫人号”来到中国,入黄埔港时,未等清兵鸣枪欢迎,竟自鸣放礼炮,误击清驳船,致二人死亡。炮手逃逸,清廷命英商馆交人,协商未果,拘捕其大班史密斯,并以官兵封锁商馆,发出最后通牒:两天以后,若不交嫌犯,立即断水断粮,停止贸易,洋船禁止回国,兵丁登船搜查。
按《大清律例》,“鸣炮误伤”不判死刑,无非杖责或流放而已,即使判了死刑,也不会立即执行,而是囚于牢房中——“监缓”,苟全其性命,偶尔还能赎罪,若其死罪难逃,至终审,尚有审批程序,一拖数月,甚至累年。况且《律例》中还有“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”的规定,地方官员不敢断案,最终报到了乾隆皇帝。
帝曰:以夷法不以民法,“自应一命一抵”。按大清律,以失误杀人,罪不至死,也可判个“斩监侯”留一条活口。可乾隆帝偏要坚持“华夷之辨”,要求以命抵命,此举,有法不依,必须听命于圣旨,这哪有法治?
何以乾隆帝要采取霹雳手段来过问此事?是就事论事,还是别有其针对?如果来者不是那些走私的“史密斯”们,而是东印度公司的人,他或许就不会龙颜大怒,而会从宽处理?
关键是自由贸易——走私,这些人不懂规矩,走私至此,就已经冒犯了“广州体制”的戒律,还有炮手失误,打死二人,那就更是在炮打天朝上国了,不严打一下还怎么做皇帝!
于是,两广总督孙士毅派兵封锁英国、法国、荷兰等国商馆,以断水断粮施压,最终,迫使英方交出一名印度船员顶罪,该船员被迅速处决,清政府要求外国商人观刑以震慑之。
这就引起了中西法律观念的冲突,按照清朝的司法逻辑,所有涉外案件,都应该坚持“华夷之辨”的双重标准。
此标准,出台于1743年乾隆处理澳门华洋命案的谕旨,其核心内容有二:一是明确司法主权,澳夷杀人,罪应斩绞者,饬由中方主审,澳葡仅能配合;二是确立“华夷之辨”的司法逻辑——华人杀害外国人可从轻发落,但外国人杀害华人必须从严抵命。1744年,根据这一不平等原则,制定了《乾隆九年定例》。
《定例》规定,澳门涉外命案,由粤地官员与澳葡“会审”,并掌握最终审判权。此举,按下了澳葡推行“治外法权”的企图,但澳葡不服,1748年,又涉华洋命案,澳葡再次包庇凶手,清廷以断粮施压,迫其交出罪犯。此类冲突,源于“华夷之辨”,给“天朝上国”带来司法不平等和程序非正义的“法欠”。
“法欠”问题,埋下了“治外法权”的伏笔。欠账,总归是要还的,“法欠”的帐,那就用“治外法权”来还。
西方列强揪住清朝的司法双重标准不放,斥之为“野蛮”,但他们自己从来不曾反躬自问:若真的“野蛮”,他们为什么还要源源不断、依依不舍地投入到“野蛮”的怀抱里来?
况且,他们一来,就来了两百多年。开放了,他来。闭关了,他也来。不开门,就敲门。敲不开,就打门。打不开,就走私。走私违法,起了冲突,就发动战争。打赢了,就殖民。打不赢,接着做贸易。总之,就是不走。
皇帝以为,他们会感恩,按照中国人的习惯,应当客随主便,随遇而安。但列强就是列强,从葡萄牙人到英国人,虽然各有其利益,各有其念想,但他们都一样,都要“治外法权”,这就更加提醒皇帝,不能掉以轻心,要加强“华夷之辨”。
于是,“天朝”与“藩属”观念,成为涉外司法的法理基础。不过,用对付葡萄牙人的那一套老黄历来对付英国人,显然过时了,英夷或能忍耐一下,但他们不会像葡萄牙人那样带着不满一直忍下去,一旦时机成熟,他们就会报复,起来反扑。
英夷之于“正义”的嗅觉,有着猎狗鼻子般的灵敏度,稍有冒犯的味道,便觉其“人权”受辱,钦定的“华夷之辨”的双重标准,居然高于《大清律例》里规定的条文,误伤致死者如为华人,可酌判流放或死缓,若为夷人就只能“一命抵一命”。
对此,英方认为,清朝司法不公,此案未经正常司法程序,直接处死嫌犯,违背了“斩监候”惯例,故东印度公司拒交船员,要求依法审判,并强调“证据不足时有权不交人”,这种对清朝司法主权的抵制,成为后来“治外法权”诉求的起点。
此次事件中,东印度公司态度暧昧,既试图维护自身商业利益的现状,又受制于中英法律冲突和殖民扩张需求。
事件发生后,英方先是转移肇事者,以消极应对,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主任威廉·亨利·皮古(WilliamHenryPigou)迅速将炮手亨利秘密转移至澳门,拒绝向清政府交出凶手。皮古认为,PG电子官方平台英国士兵不应受中国法律审判,清政府若无法抓到肇事者,案件可能不了了之。公司大班——另一位史密斯,甚至建议船只驶离,但因清军已封锁港口,而未能实施。
由于法律观念的冲突,公司大班对清政府的“连带责任”原则不满,认为“一命抵一命”违背了英国的法律精神,他们强调,英国法律要求“个人犯法由本人负责”,而清政府却通过逮捕大班和封锁商馆进行施压,被视为“极其野蛮”的表现。
但应该注意的是,公司的抗议,是基于法律,而非“自由贸易”,在反对走私——“自由贸易”这一点上,公司与清政府的利益一致,故要求法律的冲突不要转化为贸易冲突。
所以,在清廷切断贸易、断水断粮并围困多国商馆后,公司为恢复贸易,被迫交出一名船员——或曰其并非原犯,对此,清廷却不追究,不问真假,只问服法,问你服还是不服?
很显然,这是对“广州体制”的维护,在这一点上,东印度公司与清廷没什么两样,故其支持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,也是意在与清政府签订条约以确立其“治外法权”,并非支持那些绕开公司管辖要求“自由贸易”的“史密斯”们。
尽管东印度公司对清朝司法制度不满,但它基于“广州体制”已形成了稳定的利益链,故其高层更倾向于通过局部改良,如设立商馆管理水手,而非以激进的对抗来进一步推动贸易,因此,同英国政府存在利益分歧,公司虽然承担了马戛尔尼使团费用,但对其扩大贸易权利的目标持保留态度。公司担心使团行动可能破坏现有贸易平衡,故更强调“首要目标是不要损害现状”。
东印度公司对于“休斯夫人号”事件,从一开始的逃避、对抗,终于转向妥协,且欲以此为切入点,诉求英国在华“治外法权”,其本质,难免于殖民资本对主权国家司法体系的傲慢,同时,也暴露出清廷在主权维护和制度现代化上的双重困境。
不过,英国东印度公司对“治外法权”的诉求,还是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回应,当然,不是以条约,而是以默认的方式承认了公司享有特权。不久,这一特权,就通过在广州发生的另一案——“海王星号案”得以体现。
屈文生在《1807年中英“海王星号案”与英国在华“事实上的治外法权”》一文中,谈到英国在以不平等条约攫取“条约上的治外法权”前,就已经取得了“事实上的治外法权”。
1807年2月24日,商船“海王星号”上有52名水手,以“上省关粮”为由,在珠江北岸“十三夷馆”地区新豆栏街饮酒后,与当地民众起冲突,事态之初得以控制,水手们被限制在商馆内。但粤民成群结队,朝商馆扔砖石,致双方再度群殴,结果,粤民廖亚登斗殴之后,在25日或26日晚,因伤身死。
27日一早,船主巴厘臣(Capt.Buchanan)便向奉命来广州统摄贸易大班事务的“特选委员会主席”剌佛(JohnWilliamRoberts)报告了廖亚登之死。同时,廖某之亲属,也向当地县衙禀报了死因,“夷人”伤毙华人,法当拘凶抵命。
案发后,广州当局要求英方交凶偿命,但“夷馆”拒交,并援引以往仅适用于澳葡地区的《乾隆九年定例》,要求粤省官宪允其会审。于是,当局不但禁止海王星号商船卸货交易,而且逮捕了保商卢观恒,卢家广利行作为担保商,须负连带责任。
僵持之后,英方表示同意接受审讯,但要求审讯在英人商馆进行,由英方设立“夷馆法庭”,行使“夷馆审判权”“会审权”,以中英双方会审的方式,对52名水手进行审讯。基于嫌犯身份同东印度公司有关,清廷竟然史无前例,网开了一面。
这同不久前发生的“休斯夫人号案”相比,别若云泥,首先是清廷对两案定位不同,“休案”处理,由乾隆钦定,定位于国体层面,以维护“广州体制”来显示“天朝上国”的威权。
而“海案”不然,当局以华洋民事纠纷视之,而欲其尽快平息,免涉“广州体制”,故其名曰“审判”实为“调解”。
施晔在《清代外销画公审“海王星”号商船水手本事考》一文中,提到了当时与“海案”有关的两幅油画——“抵达洋行”和“庭审现场”,两画作于案发当年,其作者皆为中国画家,而且应在庭审现场,画作完成时间当在庭审后不久。
两画流传至今,均有其摹本。据考,“抵达洋行”一画,有四种版本,真摹难辨;“庭审现场”一画,也有四个版本,一般认为,小斯当东所藏为真本,因为他本人当时就在现场。
“调解”过程——“庭审”,是年4月,开庭三日,六位主审官。画面上,陪审人员共有九位。右侧四位,为中方陪审员。左侧五位,为英方陪审员,其中一位青年为乔治·斯当东,时任特选委员会秘书及商馆翻译,也为此次会审翻译。会审期间,能在法律上中西会通,便得益于这位小斯当东。
何以称其为“小斯当东”?盖因其父斯当东当年曾为马戛尔尼副使,带着十来岁的儿子一道访华,还一同谒见了乾隆皇帝,皇帝对使团没兴趣,对这位少年却颇有好感,以此为契机,故其名遂以“小斯当东”而流传。返英后,他入学剑桥大学三一学院,不久,即由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批准,聘任为广州商馆文书。刚上任,广州就发生了一起命案——“朴维顿号案”,小斯随即以其翻译身份,参与该案件的各项交涉工作。
“朴维顿号案”滋事者,乃英舰“马德拉斯号”附属侦察船——“朴维顿号”上的船员。案发后,当地官员同该舰舰长“的力士”和公司商馆“特选委员会主席”末吉合展开了谈判。
因该案受害人蒋亚有在“辜限”内并未死亡,华官对该案不再追究“夷凶”刑事责任。而英方,则以在粤英人不谙华律为由,为使英人遵法,而求《大清律例》一部,粤督吉庆未予全本,仅摘抄与杀人罪相关的条文——“六杀”,令其遵从。据这所谓“六杀”律例,小斯言,中国并非“无法”,其法亦非“任意”,乃严格编纂而成。
从此,小斯开始了对《大清律例》的翻译,他选择嘉庆版,因其更贴近清廷实际司法运用,其翻译策略,先译“六杀”,与会审联动,以双重叙事,一方面肯定《大清律例》的“条理性与逻辑性”,另一方面又抨击其缺乏“个人自由”和“程序正义”,不仅传递法律条文,更通过注释和案例,解析大清的司法逻辑。
故当“海案”再起时,他已熟读《大清律例》,并将其用于“海案”中,不但以“证据模糊”“不可信赖”为由拒绝交凶,且以会审机制对清朝司法做了一个转化——从刑法到礼法。
所以,我们比较“休案”与“海案”,就会发现,英方不同以往,已能深入《大清律例》为其开辟司法“人权”空间。
公堂上,未见有任何刑具,过堂时,原被告亦未被令跪在跪石之上,52名涉案英国水手,五人一拨,被传唤到庭,挨个过堂,站立接受法庭讯问,其余四位,交头接耳,等候审问。
还有三位衙役,肃立在堂,左右各备一桌,供庭审纪要,中英双方各派书吏一位,分别以中英文,记录庭审过程。
堂上,除审判区,皆为旁听者,约有300人,两名英舰士兵,持枪立于商馆入口,刺刀出鞘,另有两名红衫士兵,维持秩序,舰长曾经提议,欲派更多红衫守卫,向法庭致敬,但被中国行商婉拒,暗示英方,若如此安排,易生恐惧,而非表达敬意。
做到这一点,除了清政府对案件的定性定位,及其与东印度公司之间对于维护“广州体制”的默契,也同英方对《大清律例》不遗余力的搜求,以及作为中国通的小斯的译介作用有关。
中国法制“礼法并用”,存在两个空间,一为礼法空间,一为刑法空间,当然,也可有两个选择,一个选择“趋于礼”,一个选择“立于刑”,小斯深谙此道,对准了中国礼法的榫卯,符合了大清当局的味道,故能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——趋礼避刑。
“礼之用”的结果,便是用礼从宽,将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把斗殴致死转化为过失杀人,将刑讯转化为会审。
本案初查、初审,皆为南海县,二审为广州府,三审为广东省按察使司,四审为广东督抚,督抚例行上奏皇帝,待刑部复核,再由皇帝裁决。于此过程中,可见明显的转化痕迹。例如,南海县与广东督抚对案情的叙述便多有出入,前者出于案情本身原委,后者重在维持“广州体制”大局,故其题奏本内,省略了个别重要情节,如初审于“夷馆法庭”,由中英双方会审,主审官为广州府候补知府,督抚题奏时,便省去会审一节,改为南海县知县,经其一番转化,“斗杀”转变为“过失杀”。
督抚题本经由通政司转达内阁,内阁票拟后,呈帝御览。1807年12月6日,嘉庆帝降旨:“刑部议奏。钦此。”12月8日,内阁奉此,将题本及谕旨抄出交刑部,题本提要如下:夷人压核扇,因在楼支开窗扇,木棍滑落,棍头碰伤民人廖亚登身死。
由此可见,案情越往上走,就越是大事化小——讲政治,到了皇帝诏曰,皇恩浩荡一下,就春风化雨,惠及夷人。
不过,转化归转化,刑可免,PG电子官方平台罚不可免,对于肇事者,虽然仅仅罚了14两银子便了事了,在代表英伦皇家海军的舰长面前,也给足了东印度公司的体面,但“礼之用”的背后,其体制成本和人事成本,较之罚款,则多了去了,据说,“海案”保商卢茂官花费了五万两银子,用于上下打点,让死者家属、证人等封口,以及一审、二审、三审、四审各级官员分润,使各方均感满意。
可皇帝何以默许?小斯给出了他的回答:对于一个建立在如此足以唬鬼瞒神、精心策划的故事之上的裁决,皇帝当然不能轻易便对地方政府的判决、刑部的公正性进行指摘。
由此看来,他虽然熟悉《大清律例》,却不懂得中国皇帝,在皇上眼里,草民之死,不过风暴吹起一粒沙子,根本不值一提,他“钦此”的,并非此案死者,而是由此引发的“广州体制”的危机,在维持“广州体制”的框架下,对东印度公司“用礼从宽”,是天朝的既定方针,也是大清基本国策,粤官之于“海案”的处理,就基于这样一个前提,遵从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的原则。
因此,从表面看,从“休案”到“海案”,十余年间,英方在“司法主权”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,清朝之于“休案”,高压威慑,强制抵命,看似突出天朝权威,实则暴露司法缺陷——“法欠”,被英方当作了诉求“治外法权”的起点。而“海案”中,英方通过外交博弈,争取到“会审”机制,使清朝司法权威明显被削弱,这又被英方视为其“治外法权”实践的一个里程碑事件。
这样说来,当然有它的道理,但那是用了“帝国的眼光”来看中国法律,一眼就看到了中国的“法欠”,不但紧盯,而且追究,顺藤摸瓜,摸出其“治外法权”。故以“帝国的眼光”回眸,从“休案”到“海案”的这一段历程,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进展——从被迫交人偿命,到设立“夷馆法庭”,并进行公开“会审”。
但在当时中国的立场上,并不认为自己退让了主权,甚至不认为自己做了多大的让步,两者的区别,并不取决于国际政治和国际法,而是取决于清廷用礼还是用刑的选择。
在大清当局看来,它只是针对不同的对象,采取了不同的手段,但目的都是为了一个,那就是维护“广州体制”。
“休案”用刑,用刑从严,属于“严打”,何也?以其走私,破坏了“广州体制”;“海案”用礼,用礼从宽,属于“礼教”,何也?为了与东印度公司一同维护其“广州体制”。
别忘了,所谓“广州体制”,还有另一个称呼,叫做“天子南库”,它是白银时代的产物,谁敢断了它的银路?
